探索一种新的童话诗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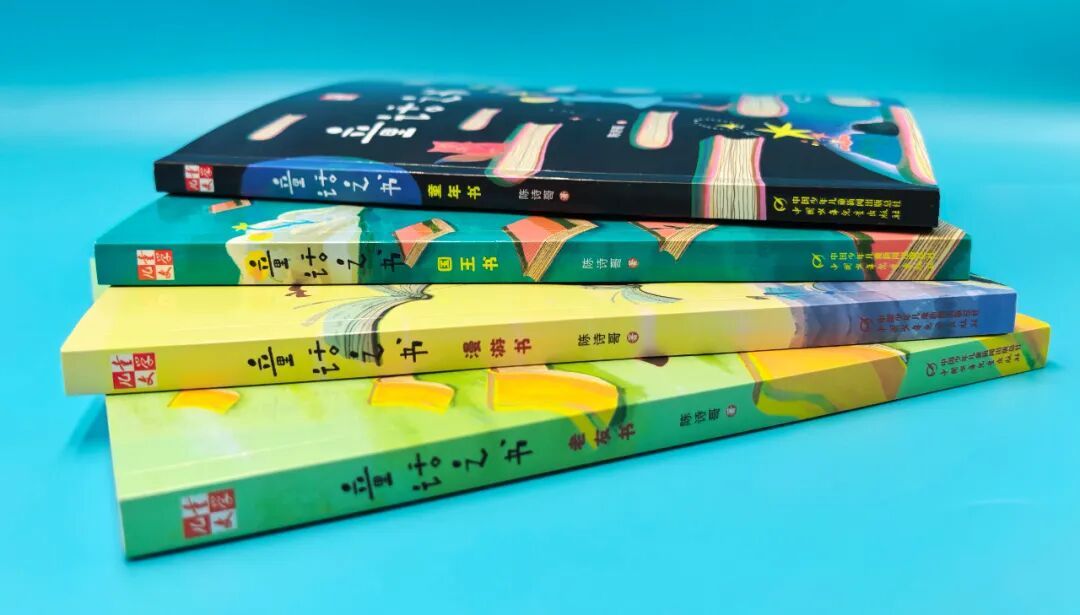
探索一种新的童话诗学:评陈诗哥第二次重写《童话之书》
涂明求
摆在面前的,是《童话之书》的第二次重写版(《童话之书》第一版是在2009年,随后陈诗哥进行第一次重写,于2014年出版)。陈诗哥一而再地修改《童话之书》,究竟是为什么?
相关的例子有很多,金庸先生三易其作,曹雪芹“批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,歌德的《浮士德》,前前后后甚至用了六十年才最终定稿;我印象中最有趣的修改轶事是关于列夫·托尔斯泰的,据说当初托翁写完“史上最伟大小说”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初稿后,“又双叒叕”地重写了八次,甚至于印刷厂都已排好版马上就要开机付印了,他还在源源不断地追来新修改,最后,印刷厂老板情绪崩溃地回他一封电报:“亲爱的列夫•尼古拉耶维奇,看在上帝的份上,住手吧。”列夫·托尔斯泰的名言是:“写作而不加以修改,这种想法应该永远摒弃。三遍四遍——那仍旧不够。”若以此话衡量,陈诗哥《童话之书》的修订之路,还“路漫漫其修远”着呢。
在聊天中,诗哥向我坦言相告过,他重新《童话之书》的直接动机,是因为感觉之前版本的语调“太过狂妄”,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,让他很惭愧。或许,青春就该是这样子,正所谓“年少不轻狂,枉为少年郎”。但随着时间流逝,他更喜欢现在的语调,大概这也是随时间而来的:热情、童心盎然,同时又理智清澈。并且,诗哥认为“童心盎然,理智清澈”也符合本书中“童话之书”的形象:童话之书历经千百年,应该是一位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。此外,这当然也是童话智慧的体现。诗哥还坦言,他所以选择这种叙事方式,另有一层关于理论的考虑在,就像罗素在《西方哲学史》中所说:“理论”原是古希腊奥尔弗斯教派的一个词语,原意是“热情的、动人的沉思”。诗哥赞叹说,这个定义棒极了,原来“理论”也可以是热情的、动人的。
这番推心置腹又明心见性的解释,既加深了我对《童话之书》的理解,也让我对诗哥平添一分敬意。而且,从他这番自述中,我们还可以发现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,其一是“语调”。切莫小瞧“语调”,窃以为,无论是解读作家,还是解锁作品,努力抓住其特有“语调”都极关键,诗哥持相同观点,他甚至极言,“我认为语调包含了一个作家的所有秘密。”恕不在此对“语调”展开讨论,但仍想“额外”推荐一篇相关佳作,我个人特别喜爱的金波先生的小童话《自己的声音》,多么温暖的灵魂文字,真正值得每一个孩子用心聆听、寻找、发扬光大的“中国好声音”。而且你会发现,金波和陈诗哥这两位儿童文学作家使用的虽是不同词语,表达的观点却相当一致、发人深省:每个人都应努力找到自己的语调,自己的声音,这是顶顶重要的。至于在《童话之书》具体的“语调”修改中,都有哪些精微之处,就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去对比去发现去挖掘吧,在此仅举一端,那就是三个版本的开头,它们是有微细差异的,以最新版开头来说,它是诗哥几经斟酌,并参考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朋友意见后,才确定下来的,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其二是关于理论,诗哥引述的罗素那句话,难得在于,现今已鲜少有人从这样“古老的”角度去看待理论问题,而他不仅作如是观更加是身体力行,也让我们重新思考,童话原来可以是另外的样子,童话理论原来可以是另外的样子,甚至你会惊觉,它们另外的样子可能竟然是它们本来的样子。
而且,正如在比较阅读中所见,陈诗哥修改的不仅仅是“语调”,还有很多、很复杂、很细腻深刻的东西包含在内。这方面,还是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最准确。在2023年末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创刊60周年座谈会发言中,陈诗哥用一句话阐明他重修《童话之书》的深层动机,是为了“重新探索作为价值观、方法论、生活方式的童话到底是怎样的”。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,学术含金量十足。我敢断言,要不了多久,定然会有更多的童话研究者注意到它;若以之为线索,按图索骥般经由《童话之书》各版本兼及其它,一步步地将中国童话诗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更为鲜活、独特、广阔、精深的新高度、新境域,也未尝没有可能。到那时,这本奇书,在某种意义上将作为一本珍贵的“源头之书”而存在。
说《童话之书》是“奇书”,绝非溢美之词。我的判断首先是基于,目前我们读到的至少99%的童话都只是在讲故事,各种各样让人脑洞大开的幻想故事,这部《童话之书》固然也在讲故事,奇特处在于,它居然是一部“童话之书”的自传;不仅是自传,它还是童话指南,有机有趣地串联起灿若星河的古今中外童话故事史,为读者担当起了童话名家名作好向导;最不可思议的是,它还跟学者“抢饭碗”,同时肩负起探察童话边际、探究童话本体、探秘童话“生长肌理”(冰波语)的学术重担。简言之,这本书在为孩子们讲好故事的同时,还在为童话创作与理论开疆辟土,致力于重述或再造一方童话诗学新天地。如此大胆、非凡,迎难而上,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。据我所知,当初《童话之书》尚处于构思阶段时,就有儿童文学理论界前辈闻讯劝诫陈诗哥不要写,因为大概率会失败,吃力不讨好,但陈诗哥仗着年轻勇于尝试不惧失败,居然一口气给写了出来,而且很成功,当然围绕此书,这些年并非毫无争议,但作为以童话探讨童话的首创之作,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。在接触此书前,我读到过很多“以诗论诗”的诗作,也读到过不少“以故事论哲学”的作品,但说到“以童话论童话”,这部《童话之书》确系目前我所见到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,不对,且慢,若加上其修订版,实则可算得三部奇书了,因为每一次的重修,都融入了作家新的思考、转变、修正与推进。用陈诗哥自己的话说,他在“重新探索”。
忘了是在哪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:探索是人类除生存外的第二本能。孩提时代的我们,距离这探索的本能最近,或者说与这探索本能根本就是浑然一体,试想想,《西游记》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《海底两万里》《流浪地球》《三体》等书为何那样招孩子们喜闻乐见?尽管陈诗哥的《童话之书》几经修订,日臻完善,但我还是更愿意把它及其修订版看做“未完成交响曲”,因为“未完成”,反而有更充足的发展空间,有更多的可能。有人说,陈诗哥之所以要对《童话之书》一改再改,是想要铸造经典,这样说当然也没错,至少实际效果就是如此,但我个人更看重的,是书中显露的他思想的独特鲜活,他对于童话的思考从未僵化、从未止步,他一直都“在路上”。也许他的探索不尽完美,尚有可改进完善处,但就像书中所致敬的童话先贤安徒生、圣埃克絮佩里、于尔克·舒比格等人一样,试问他们之中又有哪一个不是拓荒者、探路人?不倦不断的“探索”或“重新探索”本身,正是陈诗哥及其《童话之书》最可宝贵的品质。
关于陈诗哥为何要重写《童话之书》,我手中其实还有别的好回答,就闪闪发光地躺在我的《童话之书》旧版扉页上,是诗哥的几句亲笔题赠,拿它来做答案,更是精彩:读童话,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孩子;重新成为一个孩子,意味着生命如节日般归来。
本文刊发于《文艺报》2025年9月15日

